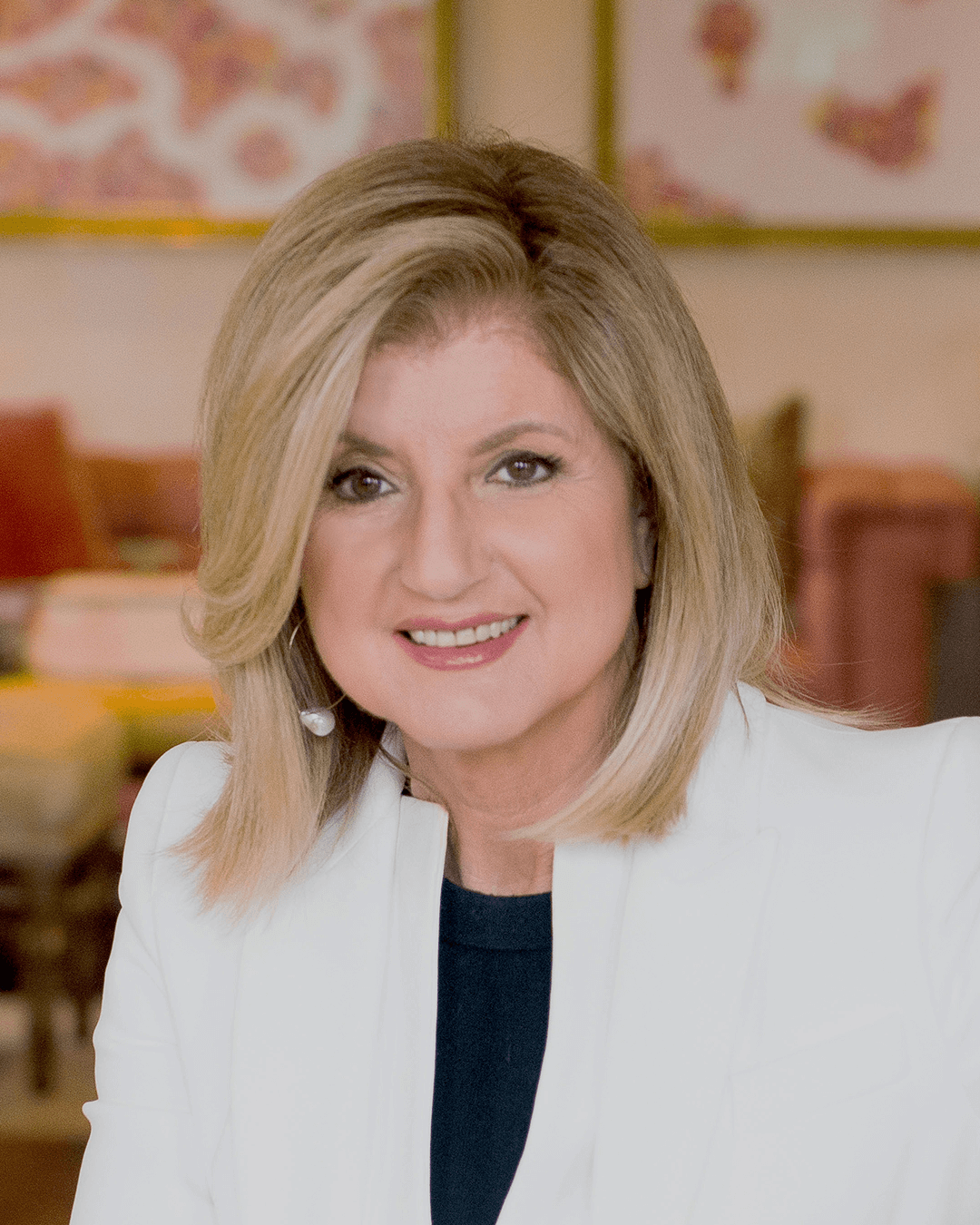渡过悲伤的浪潮:没有路线图的哀悼过程

婚礼当天,我是凌晨4点起床,无法入睡。我的未婚夫戴维着睡着时,我爬下了床,tip着脚尖through着脚步走,这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空调酒店套房,因为7月4日这座城市空荡荡的日。我走上露台,欣赏帝国大厦的美景。漆黑的城市只有几盏灯像萤火虫一样向我闪烁。温暖,麝香和潮湿。
我对前一天感到不安,但不是出于任何常见的新娘原因。
不,我很紧张,因为我不想因父亲最近的去世而悲伤。他已经六个星期前去世了,由于没有葬礼,我们的婚礼将是全家人第一次见面。我们将纪念他,让他的缺席被视为真正的损失。
然而,我对嫁给我充满爱心的未来丈夫感到非常高兴,就是使它保持一个整体。我愿意坚持下去,不要陷入抽泣的混乱中。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直期待着我父亲过去几个月的去世,甚至在他的第四阶段肾癌发生之前。但是他已经奋斗了四年。在纽黑文的Smilow癌症中心接受了一周的临终关怀之后,我从那里给他读信指环王并给他播放了他最喜欢的Eric Clapton和Beatles的歌曲-他的最终离开感觉很轻松。
在治疗中寻求帮助
父亲去世的那天,我抬头看了一个治疗师今日心理学在线列表,并与他们联系以安排约会。那天晚上,我向继母说了再见,然后回到纽约,收集了我学生的期末论文。第二天,我在期末会议上会见了学生,转回了已评分的作业,聊天并交换了愉快时光,并花了接下来的18个小时进行评分。
第二天早上,我将要求分级的决赛提交给英语系,要求打印纸本,并参加了两次会议。我乘坐下午2点的火车回到康涅狄格州,在那里和我的继母呆了一个星期。第二天,我在线提交了学生的最终课程成绩。至此,我的教学年结束了。
现在,我可以解决自己的悲伤,就像待办事项列表上的其他任何项目一样。
在我第一次接受治疗时,我表达了我的愿望,即“通过悲伤加速”。我解释说:“我想做正确的事-达到150%,最大程度地消除悲伤,这样我就可以克服并继续我的生活。”
我的治疗师笑了。她说:“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我的脸掉了。 “你什么意思?”这不是我希望听到的。
“您可能终生对父亲感到悲伤。”
在生命的早期,我从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就受益匪浅,在2015年我父亲患了癌症后不久就去看了一名治疗师。有一次,我说过一些关于需要与父亲恢复关系的事情。
我的短期治疗师曾说:“这不一定取决于您。” “您可能不会靠近。在父亲去世之前,您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父亲想要的东西。”她的话打动了我,但也帮助我弄清了我与他的关系想要的东西。
在他被诊断后,我看到了我父亲更多的东西。经过三年多的与他和我的继母在康涅狄格州的频繁访问,在他对化学物质感到不太恶心的时候,我给他做了法式吐司,陪他去看医生,并带他去了海滩和大麻药房,我们建立了更好的联系。我们看了老电影,危险!和糊状物重新运行。在2017年8月他的生日那天,我拿起月食眼镜,我们看着康涅狄格州海滩的部分日食。父亲一辈子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重要的。
即使为他的死作了种种准备,悲痛仍然震惊了我。
我不再记得应该做的任何事情。我以前喜欢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感到兴奋。我不想要任何平时的舒适食品,而是偏爱碗纯干酪。当我应该从事独立的暑期项目,准备暑期课程,撰写自由文章以及为婚礼做准备时,日子却漫长而乏味,充满了惰性。
我想做的就是玩一个虚拟的农业视频游戏,我的未婚夫戴维(David)也向我介绍了我的视频游戏–耕种泥土方块并浇灌我想象中的西红柿和花椰菜。由于心情愉悦,给我想象中的奶牛挤奶特别令人满意。关于这个田园世界,最好的事情是:即使我无法应付自己想象中的牛和想象中的蔬菜,也没人会在意。甚至赌注都是虚构的。
我向亲爱的朋友和新婚夫妇解释了我对婚礼的担忧。 “我只是害怕自己会崩溃,因为我的情绪是如此难以预测。在此之前,我可以预测自己是否能够完成某些工作。或者,如果我处于放克状态,我可以猜测何时可以恢复正常。”
“你可以预测自己的情绪吗?”她难以置信地问。 “太棒了。”
我想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可以预测的人,我心想。我的情绪通常感觉就像我可以看到的天气模式-通常我可以驾驭它们并为风暴做好准备。我想知道我的悲伤经历是否像别人的情绪波动更加不稳定。
在婚礼上,即使我的朋友们蓄势待发,如果我分崩离析,可以救我,我也很好。那天晚上,当我的头撞到枕头上时,我知道我无所畏惧。那天真是神奇,我在最重要的时候坚持住了自己。现在我可以放松了。
血清素有什么用
了解悲伤的阶段
我决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以试图了解自己的悲伤过程。如果您愿意的话,一个悲伤的人的“悲痛指南”。这主要是因为谷歌搜索“如何处理所有这些悲伤?”结果令人不满意。
首先,我发现 五个阶段 悲伤-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简直不足以形容我的绝望情绪,绝望感,无所作为的日子,一阵麻木以及最终开始恢复功能。是的,仅几个小时的睡眠后,我不再每天凌晨4点醒来。但是不,我没有“更好”的感觉。然而。
然后,我与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大学的副教授米歇尔·福特(Michele Forte)博士联系,他是悲伤的顾问,经常教授关于悲伤和悲伤的大学课程。我告诉她我正试图更好地了解我的悲伤过程。福特博士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悲伤。” “不过,它和个人一样独特。悲伤束缚着我们所有人。那就是让它令人恐惧,那就是让它美丽。”她解释说:“悲伤就像是大脑的创伤。最新研究表明,悲伤照亮大脑区域的方式与正常功能不同。它留下了持久的生物烙印。”
她还介绍了悲伤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五个悲伤阶段最初是在1969年开发的,用于描述绝症患者如何理解自己即将来临的死亡率。从那时起,“阶段理论”被广泛用于描述幸存者如何应对亲人的流失。
但是,根据阶段来定义悲伤的危险在于,人们(包括我自己)可能会错误地认为阶段存在于线性路径中,就像一组电子游戏关卡一样。完成否认,检查!现在,开始生气,然后讨价还价。或者,我们可以想象,虽然每个人的阶段发生的时间不同(以不同的顺序或时间增量),但一旦进行了讨价还价,您就无需再进行讨价还价了。对?错误!
寻找意义
梅根·奥罗克(Meghan O’Rourke)在《纽约客》的一篇题为《悲痛》的文章中 追溯了从库伯勒·罗斯(Kubler-Ross)创作“舞台理论”的轨迹到悲痛的文化区划,这是一种令人发狂的美国对悲痛过程进行消毒的手段。
奥罗克(O’Rourke)写道:“也许悲伤的阶段理论很快流行起来,因为它使损失的声音可控。”奥罗克补充说:“库伯勒·罗斯(Kübler-Ross)在生命的尽头,她意识到我们对悲伤的理解已经走入歧途了……她坚持认为,这些阶段“绝不是要把凌乱的情绪塞进整齐的包装中。”没引起注意,也许是因为悲伤的凌乱使我们感到不舒服。”
实际上,悲伤的五个阶段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兄弟姐妹:“意义”。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在他的书中发表了对此新“第六阶段”的论证和解释, 寻找意义:悲伤的第六阶段 。凯斯勒(Kessler)是库伯勒罗斯(Kubler-Ross)的合著者论悲痛,他认为找到意义是哀悼的最后一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悲伤带来的其他情绪。
在他的文章中 爱尔兰时报(Kirler)凯斯勒(Kessler)说:“直到我21岁的儿子去世,我都以为我对悲伤有所了解。” 他解释说,正是儿子的失踪使他对悲伤过程的理解更加复杂。他写道:“通过意义,我们可以超越那种痛苦。损失可能会缠绕,并且……困扰我们多年。但是,在损失中发现意义使我们有能力找到前进的道路。含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悲伤。”
婴儿多动症的早期迹象
难道“意义”只是悲伤的另一个选择吗?一旦我们弄清亲人的死亡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吗?继续前进意味着什么?
突发性悲伤与预期性悲伤之间有区别吗?
在我父亲去世四个月后的9月15日,我周日早上在附近的咖啡店里写作。突然,我的丈夫戴维(David)出现了,喘不过气来。
“我需要你现在回家。”这些话从他的嘴里滚了下来。
我关闭了笔记本电脑。 “发生了什么?你还好吗?”
“珍妮昨晚去世了。”他的眼睛充满了眼泪。
“你的表亲?”我难以置信。
大卫的堂兄比我们年轻,她是30多岁的健康,快乐的中学美术老师。她和她的丈夫在两个月前的婚礼上与我们一起庆祝。我们得知那天早上她在一场车祸中被立即杀害。
大卫和我安静地走在一起,手挽着臂,泪水滚落在我们的脸颊,九月的阳光沐浴着我们。
后来,我向福尔特医生询问了突然和预期的悲伤之间的区别。 “与我父亲不同,没有人能想到这种情况。”
她回答说:“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相同的过程。最初的反应可能有所不同,但任务仍将继续存在,还有“悲伤的调解人”。”
根据威廉·沃登(William Worden)的说法, 悲伤辅导和悲伤疗法 在悲伤阶段理论的扩展下,哀悼的四个任务在“五个阶段”结束的地方开始:
- 接受现实的损失
- 处理悲伤的痛苦
- 适应一个没有死者的世界
- 在开始新生活的过程中与死者找到持久的联系。
为此,Worden还介绍了七个“悲伤调解人”,其中包括:
- 死者是谁
- 附件的性质
- 该人如何死亡
- 历史的前身
- 人格变量
- 社会变量
- 并发压力
福特博士还向我介绍了乔治·波南诺(George Bonanno)博士的工作,他发现了悲伤恢复期间存在“复原力”。与悲伤阶段理论中的假设相反,每个人都会经历类似的悲伤表现, 博南诺博士反而发现 “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方式存在巨大差异。” 他解释 坚韧的苦难者“能够在需要时放下痛苦,并继续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他们接受损失,重新调整对事物的认识,并继续前进。”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使我们更具韧性的特质呢?在 采访发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Bonanno博士指出了影响韧性的特质,例如“自我增强”,这有助于以积极的眼光解决困难的局面,或看到成长的机会,以及“对自己应对能力的自信”。因此,也许相信我们能够处理悲伤的经历是发展复原力的必要因素。
前进的过程
在9月的最后几天,我和David飞往加利福尼亚参加Jenn的葬礼。大卫有一个庞大的家庭,看来出席率100%。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庆祝表弟的一生,并支持她的家人。教堂里挤满了人,她的同事和学生们纷纷涌向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她一直很喜欢在头发上戴花,所以她的艺术系学生用织物制作了各种颜色的花,然后将它们固定在夹子上,以便我们都可以戴一朵花来纪念她。
在仪式上,邀请了Jenn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他们的回忆。我的丈夫戴维(David)告诉团体他多么尊重和钦佩珍妮(Jenn),他说:“我什至从未意识到我有多爱她。她是如此之光。”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天;但是,大卫和我一致认为我们非常感谢能在那里。即使我没有和他的姐妹或表兄弟一起长大,我还是觉得我已经加入了大卫的家人,不是因为血缘而是由共同的哀悼仪式所束缚。
回到家一个月后,我们逐渐恢复了正常。想念我们亲爱的家人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无所不能的经历。对我来说,在我们的婚礼和詹恩的葬礼上,在分享悲伤的痛苦时感到社区的感觉是我感到亲人的回忆增进了我的生活而不是减少生活的两个时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担心悲伤的浪潮使我不知所措,使我感到惊讶,使我尴尬或使生活中的其他时刻受挫。最终,我的情感浪潮将平息,我将能够再次预测天气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