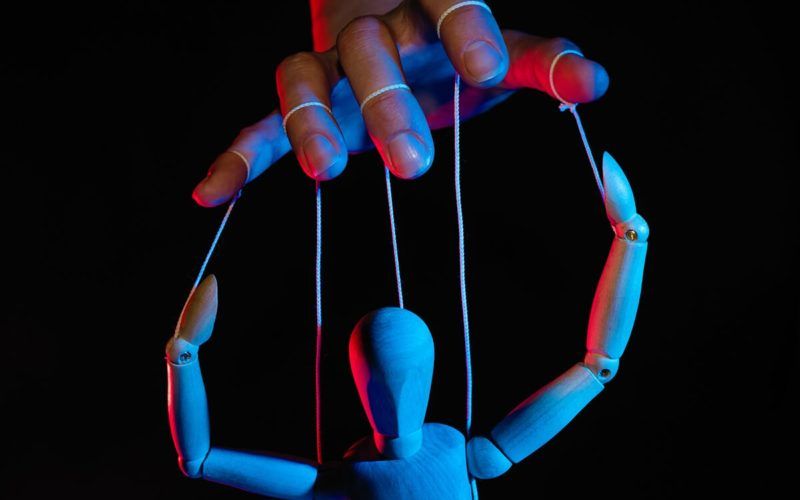饥饿:我与厌食症的战斗

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最黑暗的一天系列 ,收集了一些经历过最严重疾病的人们的故事,现在这些故事为其他人扫清了道路。
现在是早上7点,我已经在椭圆机上燃烧了1000卡的热量。我今天要收拾食物。 3蛋清和1杯葡萄的早餐热量为113卡路里。午餐将为土耳其,芥末,生菜和嫩胡萝卜提供131卡路里的热量。我还包装了1包国会议员灯,4份健怡可乐,1加仑水和1包全新的泡泡糖口香糖。下午我要上舞蹈课,另外还要学习300卡路里左右的热量。晚餐永远是万能的,它取决于周围的人和被监视的程度。我把食物保存在房间里,以备日后以防万一。我今年16岁,体重70磅;我是人类的卡路里计数器和数字天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还在Pre-Calculus中挣扎。
回顾过去,很难为所有这些事情找到一个清晰的起点。与经常描述自己的第一杯酒的酒精饮料不同,没有具体的“第一杯”。我的饮食失调是长期潜在疾病的身体表现。它是完美主义,极端敏感性,恐惧和讽刺意味的某种组合,一种饥饿感–一种对爱,接受和确认的渴望。对一切的渴望。这种饥饿感难以控制,所以我没有学会如何体验,而是自学了如何停止,切断,饿死。如果您什么都不想要,就永远不会受伤,对吗?
除了内部景观破裂之外,还有很多外部环境使我对食物产生了困扰。我住在洛杉矶的西侧-该镇以奢侈的生活,名人,整形手术和无法达到的美丽标准而闻名。在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关于冻结脂肪的广告牌,专门用于“饮食”食品的所有商店,催眠师准备说服您,当您重新睁开眼睛时,您不再饿了,人们跳来跳去告诉您多么惊人您看起来更苗条(暗中讨厌您)。即使是最强壮的心理战士,这也会使他们感到沮丧,但是当您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困惑,并拼命寻找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时–洛杉矶不是您的朋友,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有毒游乐场。
我的日子以精心计划,严格计划和可预测的制造时刻为标志。 “计划”之外的任何事情都让我陷入困境,我无法解决。我要权衡一下自己,然后根据体重秤说出是好还是不好的一天,计划好我的食物,上学,去看医生或营养师,对那个医生或营养师撒谎,回家,撒谎我整天吃饭,对医生说我正在“进步”的方式胡说八道,炮制出晚餐的一种方法,然后消失在我的房间里。那是一个悲伤的小小的生存,但是那是我的管理方式。
许多厌食症在生命早期经历过创伤,导致他们渴望获得这种控制水平。我没有那个我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感觉很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感觉。我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多年。我的父母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妈妈经常告诉我,我看起来像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想知道是否是药物在做这种事情。
随着我的医生和专家的费用增加一周,我的主要精神科医生正在推动住院治疗。我当然有100万个理由,为什么那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真正的厌食症,总是能够操纵父母同意我的观点。大学的问题来了。我进入了东海岸大学。我的医生强烈建议我回去休息一下,以使我的身体健康。到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处于最糟糕的状态。对我来说,身体上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身体燃烧掉脂肪,它就会像心脏一样以肌肉为食。我第一次同意我的医生,但是我太害怕了,不能大声说出来。因此,当我父母说也许改变风景会使所有这些变得更好时,我相信他们。
在星期二,我会见比佛利山庄(Beverly Hills)营养学家玛丽(Mary),他要我写下我所吃的一切。我迅速填好食物日志,一边撒上几杏仁和大汤匙花生酱(两件事会让她兴奋),一边撒谎。我向所有人保证,在我上学之前,我将专注于增加体重。约会之前我要权衡一下。我又减了3磅。精神病患者喜出望外,但理性的一面恐慌和我立即感到肚子疼。我太烂了。我迅速下楼,妈妈在这里存放了我们所有的健身器材,并抓住了一些小的重量。我去约会时把它们藏在书包里。在称重过程中,我总是穿医院的睡袍,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准确”的读数,从而可以轻松地将重物藏在我的手臂下。玛丽很善良,我可以告诉她,她确实很想提供帮助,但是她有点健忘,不认为要检查有什么可以扩大规模的。我继续前进,在她祝贺我体重增加的同时,迅速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所以为什么我这么难过,看数量的增加?
有一天,我走在门前,妈妈在厨房里等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脸上闪烁着恐怖的表情。她告诉我,高中辅导老师杰基曾打电话告诉妈妈,我一直在将重物藏在手臂下。杰基是我这段时间信任的少数人之一。她会把我从教室里带出来出去闲逛,在办公室里聊天,有时她会让我在巷子里抽烟。我告诉了她我大部分的秘密,但立即后悔分享这个秘密。这个谎言的发现是最后的稻草。我正式磨损了每个人的最后神经。
秋天滚来滚去,我出发去了东海岸。我致力于改变自己的方式,并在一个新的城市里重新开始。在最初的几天里,情况似乎确实有所好转。我去过食堂(对厌食症来说就像和鲨鱼一起游泳),实际上正在吃饭!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我一直飞得很高,没有任何结构,但是最后离太阳太近了。我开始失去控制,开始暴饮暴食。饥饿的岁月似乎终于赶上了。我不只是饿–我绝对满足。
我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狂欢。我记不清很多,只是短暂地漂浮在餐厅和咖啡厅内外,点餐和用餐,然后前往下一个地点。我记得几次尝试告诉妈妈和治疗师的尝试都失败了,但我因恐惧而瘫痪了。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发现了勇气,想发短信说:“妈妈,我不好。我需要回家。”
那天晚上,我降落在医院。除了母亲妈妈的鞋子快步走下医院走廊的声音外,我再也没有任何回忆。不用说,我如愿以偿。我回家了。
第二年,我参加了强化治疗计划,在那里我对自己的康复感到认真。我去了个人疗法,家庭疗法,团体疗法,在那里我们拿着刻有“希望”和“爱”之类的字眼的石头,营养课,团体餐,个人饮食,团体郊游–这些都是关于学习基本生活的技能。它正在学习在生活不可避免的混乱中如何应对,如何感觉,如何变得健康。这是在学习如何爱自己以及如何向别人展示自己。
死亡和死亡的五个阶段是什么?
恢复是终生的。没有神奇的时刻,您会突然好起来。复发在饮食失调中极为常见,我也不例外。但是,通过持续的治疗,自我护理,冥想和正念,我能够坚持到底并以一种真实而健康的方式生活。在糟糕的日子里,我感到自己会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但是今天我也有选择。
如果我必须与任何遭受苦难的人分享信息,我会告诉他们放弃控制权,并跃跃欲试。我会告诉他们,恐惧的另一端是的生活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生活可以是美丽的,丰富的,令人兴奋的,可怕的,疯狂的,充满激情的,不舒适的和凌乱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您每天需要做的所有事情都一天活着,当您以自己的方式摆脱困境时,您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