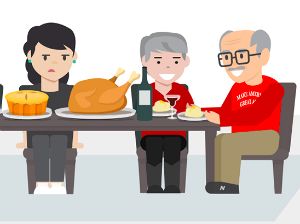有毒的爱:几乎没有我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最黑暗的一天 系列,收集了一些经历过最严重疾病的人们的故事,现在为其他人开辟了道路。
一定要花20多岁的时间,而这种方式不会引起以后的后悔。我知道22岁刚从大学毕业,最近刚和一个辍学的垃圾商人男友住在一起时的感觉,这让我很难想象。有些人必须具有性格,运气或某种组合的力量,才能跳过您的生活,因为它很快变成了您自己的发展阶段。我很好奇他们。
当我22岁时,我决定放弃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不合适的人的生活。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这一生的这段时间, 琼·迪迪翁 称为自尊,或勇于犯错误。勇于承担这个错误的勇气必须意味着我认为我最初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好吧,他有点书呆子,带有浓浓的印第安纳南部口音。他读了很多书,词汇量很大。他有些甜蜜。他一般都很友善。我认为这些是积极的特质。
我们21岁那年,他26岁那年,在一家诗歌工作室相识。那是在他与我们大学的哲学本科课程之间反复无常的关系的“一段时期”内。他开始调情。它从一个玩笑开始。然后,他开始赞美我上课的诗歌。不久之后,他告诉我我很漂亮。我以一种完全不发达的方式感觉到,他在我对我是谁或我来自什么的理解中陷入了每一个缝隙。他既崇拜又足够不能接受,以至于完全完美。
特定恐惧症的定义是什么?
不能说他具有传统吸引力。我父亲允许自己进行一次批评,这给了这个男朋友一个绰号:“伊卡博德”。他的确看起来像伊卡博德·克兰(Ichabod Crane)的旧版画,只是穿着现代服装。他很高,又瘦又瘦,长着一头卷曲的马尾辫,两次洗涤之间变得越来越模糊。他那双巨大的蓝眼睛被艰难的接触睁开了。他穿的是李维斯(Levis)牛仔裤,蓝色或黑色的汉斯(Hanes)T恤和匡威(Converse)运动鞋的日常制服,所有这些都是从旧货店采购的。他和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在我们自由大学城里有些遥远的人物。我刚刚了解到资产阶级在前一年意味着什么。他绝对不是资产阶级。我想,他有点可爱。我们开始约会。
他不会告诉我他为赚钱做了什么。我仍然沉浸在我的 大学生活 ,这是一种天堂。我必须不停地阅读,写论文和诗歌,在戏剧中表演,所有这些都是在有趣的人的陪伴下,在一个美丽的环境中进行的。但这一切即将结束。大学本来是准备。但是准备什么呢?我避免考虑这个问题。
20年代初是一个棘手的心理时期。一位挚爱的朋友和室友毕业,回到家中,很快被诊断出患有 精神分裂症 。是时候在青春期和成年之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释放出遗传恶魔。在环境方面,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压力很大。隐藏是我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选项。找一个失业,外表怪异,在雷达下,反资本主义,前哲学家的主要男友突然看起来很幸运。
我没想到我正在辍学。我以为他也许可以看到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世界。我来自农田中的一个工业城镇。在那里遇见因农业或工厂事故而失去手指的老人并不少见。勤奋是我青年时代的最高美德之一。但是也许我们都被欺骗了?
如果你有惊恐发作怎么办
的确,在我读过的每一本书中,关于他的辛勤工作的重要性,他都像傻瓜一样。尽职尽责的无聊的蚂蚁花了很长时间,但他却是只懒洋洋的蚂蚱在玩弄小提琴。他躺在地板上的蒲团床垫上,弹着吉他,谈论他如何使被新教徒的职业道德压迫的人可怜。他可怜那些珍视像汽车和新衣服这样的美国奢侈品的人。他怜悯那些为了一天退休可能会花钱而退休的人们。
当我邀请自己进入他的星球时(我的租约已经到期,我毕业了,我不想搬家,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我不知道,即使这种文化可能存在严重缺陷,拒绝加入我们所生活的文化也是一种疯狂。
他对工作一阵子co,但是最后,也许是当我搬家时,告诉我他为赚钱做了什么。他买卖垃圾。他在选定的贫穷状态中尖叫。
我们开始一起生活。有时星期六星期六早上我去探望他去寻找商品。他带回家的老式玩具,陶瓷和胶木手镯被放在厨房的盒子里。整个公寓都很冷淡,我没有试图纠正它。他不认为这很严峻。他不仅赞赏地谈论了我,而且还谈论了他的空调,冰箱和玻璃纤维淋浴间。
我砍掉了我一头长发。我体重增加了。我买了所有杂货,他付了房租。我开始在一家爱尔兰酒吧工作,这家酒吧的薪水比我以前在那家西藏餐馆的要高。第一个晚上,他接我。我对新同事说再见后,他说:“他们都是酒鬼。”我上班后也开始喝酒。和我的同事一样,有时在我轮班期间。在上班之前,我会坐在后院,几本书堆在我旁边作压载物,看着我空的笔记本而不写。
他继续告诉我,我很出色。我会从一个梦中醒来,并告诉他这件事,他会说:“你那漂亮的大脑,劳拉,你不可思议的大脑!”他告诉我,即使我的发型糟透了,我一直都很美丽,只适合我最近在院子里发现的脱掉衣服的衣服,哭了很多。我不觉得美丽。他经常抚摸我的头发,好像我是一个宠爱的宠物。
我们俩都要当作家。互相交流我们的想法非常令人满意,以至于没有必要向我们之外的世界投放任何东西。我还不知道成为一名作家需要纪律,计划和野心。如果不做写作工作,我们就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成为作家。
刚开始,我以为自己过着波希米亚式的幻想。大三时,我上过现代主义文学课,后来被Djuna Barnes和Mina Loy和H.D完全迷住了。和富有创意的女性进出巴黎,彼此的生活在1920年代。这个男朋友是如此遥不可及,对我的家人来说是如此难以理解,那么甜蜜又健谈,我可以告诉自己,这几乎就像和一个女人约会并在异国他乡生活在一起。
我存了女服务员的钱去法国旅行。他没有保存任何东西。我们一起搬家大约一年后,他放弃了公寓,我们去了欧洲一个月。我付了。它既美丽又有趣,但最终毫无意义。我们回来了。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一起搬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躺在公寓里处理虚构的工作,尽管我很快就找到了。
贫穷正在失去魅力和公义。我开始发现,不仅仅是他选择了这一生,还在于他无能为力。我开始第一次意识到,抗拒世界,如果它是一种积极的抵抗,那将是正确而美好的。但是,通过辍学抵制世界是一种悲伤,伤害,愤怒和惯性,也许最好将其称为 萧条 。
我们从未战斗过。我为此感到自豪,但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不健康。有一天,当我意识到自己处境不佳时,我开始哭泣,无法停止。我们公寓二楼的窗户外面有一场寒冷的冬雨。我不知道突然间有什么东西脱落,但是我却无法表达清楚。我去厨房煮了拉面,哭了。我带着宿舍和一个洗衣篮下到地下室,哭了。
我们去公寓大约一年了。我无法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也无法停止哭泣。午后他说:“您很失望,因为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那之后大约一个小时,我说:“您很失望,因为我不是朋克摇滚歌手。或任何朋克摇滚乐。”这些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
latuda工作需要多长时间
他只有一次威胁要暴力。我母亲正在去我们的路上,而我正在清理压力。我敢肯定,让家人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对他来说很不舒服。他知道我的母亲不赞成我们的关系。在我眼神扫地和拉直的过程中,我一定已经请他提供帮助。
他抓住我的喉咙,将我推到柜台上,让我知道这是我的事,而不是他的事。我很震惊。我不知道如何合理化那集,但我做到了。谁知道如果我再问他更多的话。除了赞美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他从未告诉过我他爱过我,可能是因为他知道爱与责任是交织在一起的。
不能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接受错误的思想很重要。但是我仍然很难原谅自己选择他。这不是最严重的错误,毕竟我只是伤了自己。但 在关系中伤害自己 也是罪过现在,我不敢相信我没有帮助那个宝贵的年轻女子。我那个年轻的女人心胸开阔,有天赋可以与世界分享。并与那个傻瓜在无精打采中浪费了很多年。
想象着其他人在我的处境中帮助我找到了出路。我意识到,如果我有一个姐姐,而她是这样生活的,我会怜悯她的。然后我会帮助她的。
我申请了研究生院,但只申请了较远的学校。我被纽约的一个项目录取,这个城市需要太多的努力才能让他跟随我。而他没有。
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我正巧搬到世界心理治疗之都。当我到达时开始接受治疗并一点也不奇怪,这对我很有帮助,并且从这段恋爱关系中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光。似乎我遇到的每个作家都已经接受治疗多年,所以,实际上,为什么不现在开始呢?我想。自从与我合作以来,我很幸运与几位出色的治疗师合作,他们帮助我看到了想象力和妄想之间的区别。他们帮助我了解,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不必留下。
自从回忆起我这一生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如果在美国,每20岁的年轻人都要接受治疗,那该怎么办?我知道这听起来太过分了。但是,实际上,如果在确定谁与谁在一起以及如何生活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有专业帮助来了解我们家庭和文化的心理,神话,该怎么办?我很高兴为自己定义角色和界限提供了帮助。我觉得自己像个布道者,但我真的希望每个年纪轻轻的人都能 尝试治疗 并找到我最终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