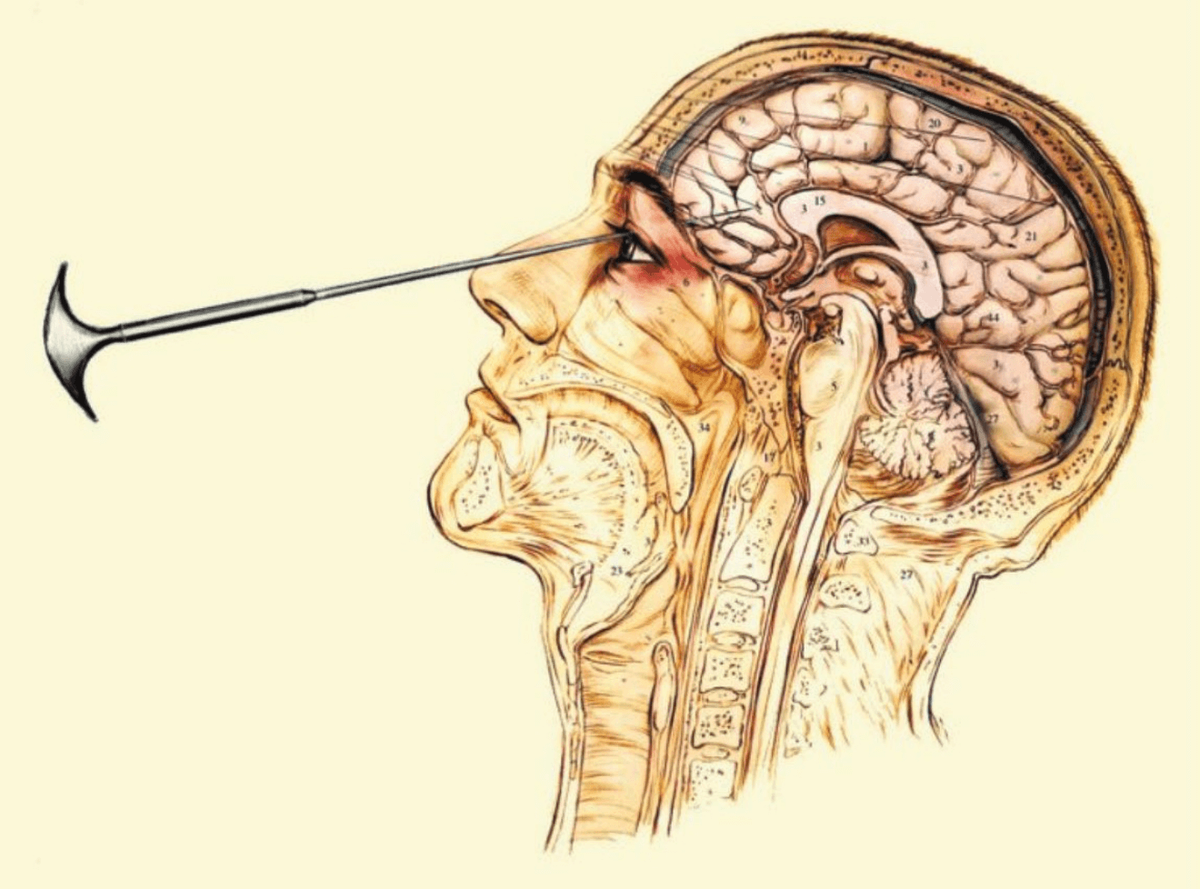身体变形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高中之前,我很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不安全。除了典型的青春期女性瘙痒看起来更像芭比娃娃(皮肤光滑,牙齿更白,头发更金发,鼻子更小)之外,令人惊讶的是,我与自己的身体保持了平静。我比大多数同学(11岁起,身高5'9”)要高得多,但是我的父母和朋友向我保证,很快,我将为自己的身高而感恩,甚至让我的朋友嫉妒。
可以预料的是,我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瘦弱的13岁小伙子,对披萨的胃口永不满足,对放学后每天吃一半的意大利辣香肠派作为点心没有任何疑虑。我的朋友抱怨他们在玩耍的时候一起做仰卧起坐时的“松弛”肚子。我讨厌运动, 我告诉了他们。
尽管现在似乎夸大了对自己的身体“冷漠”的承诺,但我从小就意识到自我形象问题困扰着大多数女性,并尽我所能对我的身体状况提出批评并警惕我收到的信号来自流行文化。我总是注意到,每当我们外出吃饭时,妈妈都会在餐厅点沙拉和调味料。其他妈妈在孩子们的生日聚会上吃蛋糕,而我的从来没有。我决定自己是那种会毫不留情地和孩子们一起吃甜点的妈妈。
我知道“我是奴隶4U”视频中的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 Spears)的腹肌本来很理想,并且在看完Paris Hilton穿着合身的工作服后,想知道我的大腿是否比大多数人大简单生活。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最大努力不关心厚度。我看到自己的抵制是对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政治上的东西的保证。当然,当时我还没有词汇。
诊断为 强迫症 (OCD)和 焦虑 在9岁那年,我发现了其他方法来解决我的控制问题。强迫性清洁,用公制尺子随意测量我房间里的物体,每当我走到某个地方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反复数四。这些是我应付的首选方式,我紧紧抓住它们,以维持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和控制感。强迫症习惯菜单上的另一个选择对我来说是卡路里计数。
直到我14岁
把你的错误归咎于他人
那一年,我的父母有严重的婚姻问题,我们的家庭暂时崩溃了。我感到自己的世界失控了,并且由于焦虑而无法进食几周。磅从我身上掉下来,我在减肥中找到了安慰。看到饥饿的影响有些安慰。随着我逐渐减轻体重,感觉好像我正在重新获得经验。这也是一种方便的应对机制:我每天都不会感到悲伤,恐惧或生气,而是会感到饥饿。能够忍受这种饥饿感使我感到英勇。不幸的是,我同时是英雄,反派和受害者。
虽然我在 治疗 在这段时间里,我现在将其确定为第一次(自我诊断) 厌食症 ,我否认自己甚至遇到了问题。我从未向我提及对食物的恐惧 治疗师 ,因为我从未对自己承认自己的任何新习惯。当我的治疗师问我如何以及为什么失去这么多的体重时,我平静地告诉她我开始跑步。最初,我在进行焦虑症和强迫症的治疗时,向我解释说,我对长跑的新发现是取得长足进步的标志-我养成了养成提高自己的情绪并控制自己的反省的习惯。 (我不是在撒谎; 行使 可以有一个 积极影响 关于强迫症和焦虑症的症状,但我的解释是我否认机制的核心内容。)
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我继续构建谎言网。我会告诉朋友:“我已经吃过饭了。” “我在厄瓜多尔有一个寄生虫,”我告诉我的美国历史老师,他经常对我的突然减肥感到担忧。我不想要帮助。我找到了一种与我的身体玩神的方法。厌食症可能使我感到饥饿和身体虚弱,但也使我感到精神上无敌。我不会只是放弃那个。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恢复了失去的体重,并恢复了“正常”健康的身高和体型。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或原因失去了继续挨饿的纪律,但我记得体重逐渐增加,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时弯曲“规则”的副产品。
depakote 的副作用是什么?
尽管我一生的体重都一样,但厌食后的身体却显得庞大而怪诞,就像我住过的一身怪兽套装,却无法完全体现出来。由于我仍然感到羞耻,无法向治疗师承认自己的饮食问题和身体焦虑,所以我唯一的表达方式是随便向亲密的朋友,姐姐和妈妈抱怨“我很胖”。
花了很多时间为我担心,他们都为我重新开始进食而感到不安,并且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因此,他们向我保证,我看起来很棒,并尽最大努力不说任何触发因素,因为我意识到我显然在努力应对身体形象和食物。
在那段时间里,我重新建立了相对正常饮食的习惯-也就是说,没有严格的限制或规则-但我的内心仍然因痴迷而动摇。即使我对食欲感到厌恶,我也不断想着食物。我担心在别人周围吃饭,担心他们会“强迫”我吃引发性的食物,以及他们会认为我很胖。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被窒息而窒息,而且离身体很远,就像在生物学课上被要求解剖一样。
如何与反社会人士离婚
我迫切希望找出自己之外的某件事或某人来指责我的失控。我约了一名甲状腺专科医生,并坚持认为我患有代谢功能异常。当我的血液检查结果表明我的甲状腺功能实际上还不错时,我前往亚马逊去探索减肥药的市场。有时,我从学校的同学那里买了以安非他明为基础的兴奋剂(例如Adderall),我知道他们有处方药。我并没有挨饿,但我的思维方式几乎和挨饿一样危险。
健康,必要,厌食后体重增加的第一波是我的“旅程”的真正开始 身体变形 (又称身体变形障碍,又称BDD)。根据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BDD是一种疾病,其特征是人们痴迷于真实的或可感知的缺陷,他们通常会以夸大的尝试来掩盖或修复它。 DSM-5认为BDD是 强迫症 ,并将其与神经性厌食症区分开来,尽管两者经常共存(通常与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并存)。就我而言,厌食症是在身体畸形之前发生的,因为直到我剧烈的体重减轻(以及随后的体重增加)才使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并以正常体重消失。
高中并不是我与厌食症的斗争的终点,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应对身体畸形。但是,列举我减肥和增重各章的细节并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故事。总而言之,我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又发生了三起急性厌食症,并伴有持续的身体畸形。在我正常健康的体重下,我常常因对自己的身体的痴迷(和非理性)想法而瘫痪,并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当我瘦弱时,我几乎无法在社交或职业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受到自我克制的能力的鼓舞。拥有这种控制的幻觉奇怪地使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更“在家”。
从上一次减肥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现在我终于可以继续保持正常体重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感到舒适。在某些日子里,我仍然感觉像是种了不起的形式。在其他方面,我还不错。我不再挨饿,实际上吃得很正常-健康但不拘泥。没有更多的减肥药或Adderall。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我面临身体变形。它的名称可能很复杂,但并不总是那么极端。消除对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化的一部分包括表明它们有各种形状和大小。这是一个频谱。
就像对任何事情的焦虑一样,我的身体畸形的严重程度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起伏。我很感激现在与 认知行为治疗师 当我练习养成思考习惯和行为方式时,他会给予我支持和责任,这会鼓励我感到更加自由—不仅在食物和身体形象方面,而且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
检查我的自我诊断的厌食病史后,我和现任的治疗师和我花了更多时间谈论全身性焦虑和身体畸形,而不是自己饮食习惯。那些身体畸形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真实或感知上的缺陷产生想法,并经常进行强迫性行为以缓解他们对自我形象的焦虑。
不用说,让别人跟我谈谈我自己的身体变形,这有助于将我对身体的想法和感受纳入视野,并帮助我与使我多年不健康的虐待性思想保持距离。当我听到身体变形的声音落在我的思想中时,我现在只是想告诉我我没有空。从这些想法中脱颖而出,而不是毫无疑问地相信它们,是我康复过程中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