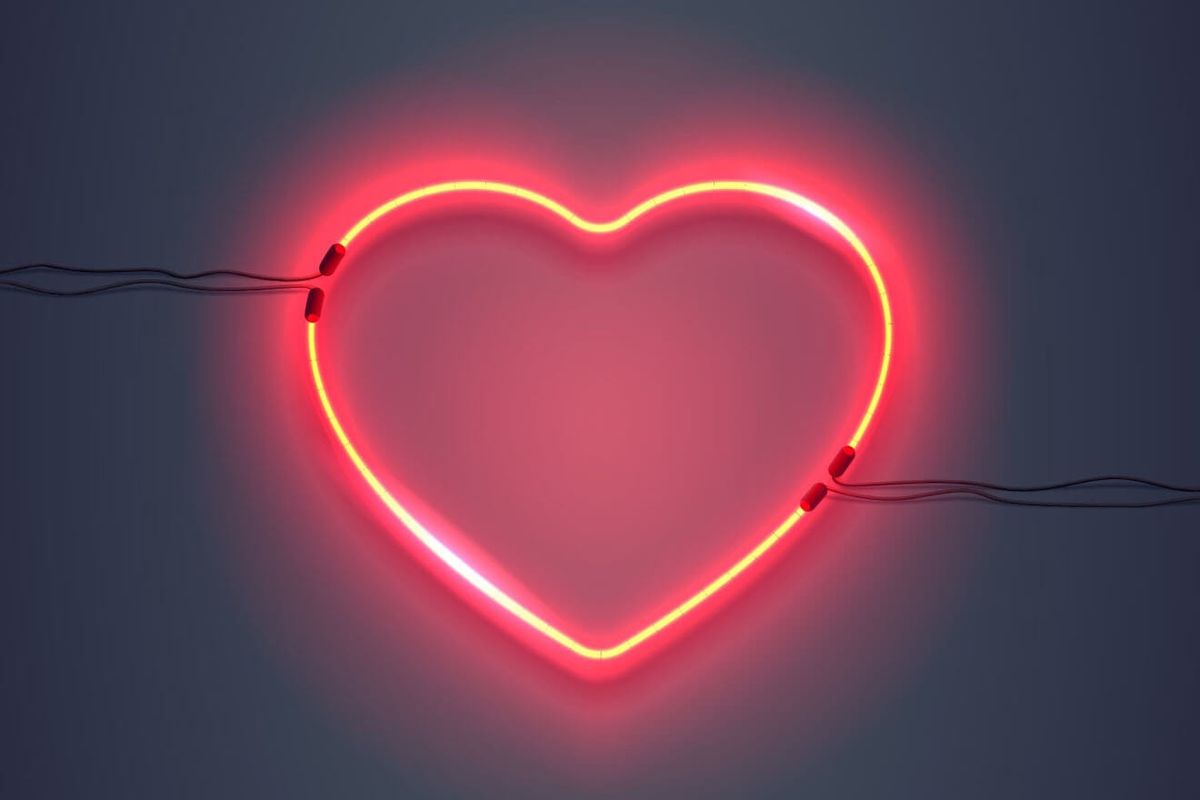中午恶魔:畅销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音频采访

德里克·赫尔(Talkspace):
您好,欢迎您-我是Talkspace临床研究与开发副总裁Derrick Hull。今天我们要与政治,文化和心理学的作家兼讲师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博士进行交流;国家图书奖获得者;也是LGBTQ权利,心理健康和艺术领域的积极分子。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临床医学心理学教授(精神病学),并且是PEN美国中心的前任主席。所罗门(Solomon)的书《最远离树》(Scribner,2012)最畅销,讲述了家庭抚养杰出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不仅学会应对挑战,而且在这样做时也具有深刻的意义。所罗门的回忆录《午后的恶魔》(Scribner,2001年)获得了2001年全国非小说类图书奖,并入围了2002年普利策奖,并被《伦敦时报》评为“十年百佳书”。所罗门与他的丈夫约翰和儿子乔治生活在纽约和伦敦,是双重国籍。他还拥有一个由女儿和约翰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
好吧,安德鲁,欢迎。我想发表一个个人轶事,说明为什么今天和您讲话如此令人兴奋。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临床培训时,我们收到了您的书,中午恶魔在我们的实验室。我们会将它传递给所有研究生。特别是对我而言,它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我认为临床培训的一个方面有时会有些问题-当我们谈论诊断类别时,就好像它们是简单还是直截了当,就像我们知道它们是什么一样-我认为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尤其如此,因为这两种疾病通常被称为“常见疾病”,这使它们看起来简单明了。
关于的奇妙事情之一中午恶魔以及为什么它真正成为我的受训者的原因是,它为抑郁症的表现方式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其含义赋予了如此丰富的质感,深度和复杂性。
而且,这本书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将您自己的内部经验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并且将其融入我们应对精神疾病的更广泛的系统方式中。这真的是变革性的。
我知道,在您刚刚添加的最新一章中,您谈到要从遭受抑郁症困扰的人那里收到来信。但是,我想知道您是否收到过学员,进入该领域的其他人员的消息,以及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你听到那样的话吗?
安德鲁·所罗门:
我确实听到过这样的人。我认为通常是那些非常希望提供帮助的人。但是,当人们感到沮丧或确实焦虑时,尤其是在沮丧时,他们常常会失去描述的能力,也无法很好地解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因此,我有很多与我保持联系的受训者,他们对我的自传部分以及我与其他遭受抑郁症困扰的人的采访都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想法感觉如何,体验如何。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您知道的,这实际上使我希望有一本关于几乎所有诊断类别的书。尽管我有点自私地说,因为您在书中反复提到写书是一项艰巨而富挑战性的工作,但在某些方面很有帮助和变革,而在另一些方面却非常痛苦。因此,要问是否会有像这样的书每一个诊断类别。
安德鲁·所罗门:
但这实际上是最终的回报,并与其他就类似主题撰写书籍的人交谈,我认为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怀疑这是宣泄的,而是您通过交谈以某种方式释放了恶魔关于它们或写关于它们的信息,更多的是,您在生活中会获得这种体验,就像一种贫瘠,干燥,无用的体验,并使其对他人有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时间。那并不意味着我会选择再做一次。如果我能在没有沮丧的情况下再次生活,我会更愿意的。但是写关于它的不仅是赎回-我是说这很困难而且很痛苦-而且对我来说也变得有意义和有意义。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当您在其中添加章节时,您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嗯,现在是四,五年前。)这是一个类似的过程吗?当您坐下来写那章时,您是否觉得自己在另一个地方?
安德鲁·所罗门:
我在另一个地方。我的巴西出版商要求我写一本介绍,以重新发行该书,然后我坐下来做。在开始时,我想,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呆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谈论抑郁症,我学到了很多我写这本书时不知道的东西。我开始写下有关所学到的不同东西的笔记。这样一来,我就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人们的生活经验。我觉得确实有必要扩大我所说的内容。不仅要介绍自从我写原始书以来出现的新治疗方法,而且要使之成为一本书,以扩展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品质或同情心。
金门大桥跳线机构
我的意思是,当本书出版时,我可能采访了30位抑郁症患者的经历。自该书问世以来,大概有15,000或20,000人向我发送了有关抑郁症的描述。它改变了您的观点,观点和紧迫感。然后,在我写那章之前,我很方便地感到了一种轻微的沮丧。因此,我也可以将其折叠在里面。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数万人。很难想象要收到人们的这种反馈,您必须拥有所有的情感和反应。
安德鲁·所罗门:
有时候感觉很有意义,我很高兴能够为人们提供帮助。我收到来信,我想:“好的,您需要去看另一位精神科医生,您可能会对这种疗法有所反应。”我非常愿意发表评论。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会再与那些提供具体临床建议的人联系,但我可以为人们指明一般方向。还有其他日子,它完全让人不知所措,我醒了,我想:“哦,不要再来了。”
我的意思是上周我收到了伊朗某人的来信。伊朗的一位妇女给我写信说自己患上抑郁症。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如果是普通字体的话,它必须长六页。我对其中的所有细节感到不知所措。我粗略地读了一下,我想:“好吧,在某个时候,我必须回到那个位置。”今天,我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个相当坚持的音符:“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需要听到你的来信。我很绝望。”有时,世界另一端完全陌生的人的绝望感到非常沉重。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在某些方面,您正在说一些我很好奇的事情,当我们坐下来为这件事做准备时,您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体验,以及您已经在说什么。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您自己的经历具有临床方面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其他人的经历也面临着挑战,并且在某些方面,这些人正在从自己的见解中寻求支持。它使您成为焦虑和抑郁症的领头羊,而这种体验感觉是如此复杂。我想知道您是否对过去的整个经历说了更多,天哪,它已经持续了19年左右。也许更长。
安德鲁·所罗门:
好吧,您变成了其中一个沮丧的人,您会发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盘旋回您所在领域的其他人。就在今天早上,我正在与一群科学家进行会晤,他们正在为更广泛的精神疾病领域的新研究提供资金,我们正在讨论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它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哦,好,我有我的大学朋友,我有我的抑郁症朋友”,只是我所认识的一群人,在赛道上的人。
但是我也感到,认识其他很多我原本只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经历持开放态度而不会认识的人,实际上使我的生活变得非常丰富。我的意思是,有很多人是熟人,甚至我会以为是朋友,他们从未告诉过我自己的困难和痛苦。书出版后,人们对此感到更加放心。我很幸运能够如此了解这些人。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在我回过头看的时候,集中精力多写本书中午恶魔在准备今天的演讲时,令我感到与众不同的一件事是,它与许多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大相径庭,这些著作都将提及流行文化,或者引用了一些研究,然后围绕该内容进行写作。中午恶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从完全不同的布料上剪下来的感觉。因此,关于编写它的问题是,当您着手进行此操作时,是否有您正在使用的模型,或者您只是坐下来开始写作?这种结构,这种特定方法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安德鲁·所罗门:
我觉得有很多关于抑郁的好书。有关于正在开发的心理药理学的书,有关于基础生物学的书。有个人回忆录讲述他们的故事。有医生写的关于他们对病人的叙述经历的书,有各种各样的书问世,有流行病学史的历史,而且我觉得没有人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我觉得如果我要去做某事,那我就要去做。我打算尝试将所有不同的思考和考虑疾病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并尝试将它们整理成某种东西,使人们能够使用所有的思维方式,或者至少是我能想到的方式。关于它。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真有趣。一种将所有不同的线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稍作调整。您知道,您已经在前面提到过,参加正在进行研究的个人。我想知道您是否有任何意见,或者想指出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或者正在准备进行的研究,这些特别令人鼓舞的,新的或新颖的,我们应该关注的研究?
安德鲁·所罗门: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突破的边缘,但是我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对抑郁症的理解在本质上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我的意思是突破...突破是什么?
您知道,这是一种深层的大脑刺激,其中将电极插入大脑的某个区域,并用于刺激患有严重,难治的难治性抑郁症的人的大脑。但是我的意思是,显然这不是很多人都会使用的东西。氯胺酮正在研究中,这表明药物实际上可以使重度自杀的人几乎立即缓解自杀感。氯胺酮存在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滥用药物。现在有许多工作正在进行,试图弄清楚如何使氯胺酮疗法对人们可用,并且比现在更容易实施。
关于psilocybin的一些有趣的新研究着眼于同样在魔术蘑菇中发现的该物质是如何滥用的-人们从其致幻作用中获取它们-psilocybin可能有什么帮助。但是就实际药物而言,没有任何新药物通过。有一些电动工具使用各种设备提供从手外部发出的电刺激,从理论上讲,它对大脑有影响。我认为这项研究没有说服力,但确实是一种趋势,而且确实存在。但是从本质上说,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治疗方法以及最好的治疗方法仍然是电惊厥疗法,其效果远不如影片拍摄时高。一只杜鹃飞过筑巢了。但是它仍然不是很令人愉快,并且可能对记忆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没有走这条路的人,我们拥有的最佳治疗方法是在过去25年中一直在使用的SSRI。
获得处方xanax的最简单方法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但是,有趣的是,您知道,在反思您对文学的印象时,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当然也担心,我们对几乎所有诊断类型的理解似乎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有了您刚才说的所有内容,如果有人来找您咨询,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说,您是否希望有一件事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心理健康?如何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安德鲁·所罗门:
我认为我首先要说的是,人们应该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寻找抑郁症的迹象时,而在整体上,在他们自己和周围的人中,要寻找精神疾病。并且认为自己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应该去找医生。您患这些疾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逆转。人们不断说:“我真的很想独自奋斗。”最初我是这样做的,但如果没有这样做,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陷入我所经历的灾难性萧条。因此,我认为人们应该理解,即使症状看起来相对较轻,也值得去看医生,并且值得密切关注症状,也值得看他们是否正在升级。因为如果您能及早,早,早得到治疗,那么您可能不会遇到这么严重的问题。
如果您等待,等待,再等待,然后继续思考,“我想我可以做到,我想我可以做到。我想我可以自己做。我想我会没事的。”那真是愚蠢。如此之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愚蠢的,他们说:“我开了这种药,但我服用的剂量非常低。”服用对您有帮助的剂量。服用10毫克Lexapro而不是20毫克Lexapro,将不会给您来生的任何回报。要做的事情是变得更好,并记住生命短暂,而花费的时间却不会变得更好,这就是您感觉不舒服的时间。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这让我想知道您是否感到耻辱是这种寻求帮助的阻力。如果是这样,那么您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几年中是否看到了耻辱的许多变化?
安德鲁·所罗门:
好吧,毫无疑问,污名没有现在那么糟糕。我的意思是,当Bill Styron写书时可见的黑暗在1980年代,没有人公开谈论抑郁症的经历。这本书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然后对许多人来说非常有价值。现在,您知道,名人到来的过程很正常,他们谈论自己的沮丧,他们谈论自己的焦虑,像Demi Lovato这样的人谈论他们的经历的各种细节,而且您肯定会了解更多公开讨论。但是它仍然受到高度的污名化,有些污名来自外面的人,有些污名来自内部。我们仍然有一个社会倾向于将精神疾病作为品格的弱点传播。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这些疾病几乎是道德上的失败,并且使正在经历这些疾病的人们从这些角度来思考它们。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当我阅读添加在其中的最后一章时,对我来说很重要中午恶魔是您提到了两个对您很有帮助的资源。一个是心理药理学家,然后是另一个心理分析师。而且我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多谈谈与精神分析人员一起为您所做的工作。您是否尝试过其他心理治疗方法?这些如何平衡您自己的需求。
安德鲁·所罗门:
与我进行治疗的人都接受过心理分析培训。我们进行了一种心理动力疗法,但我并未进行全职心理分析,而且我每天也不在那里。我想我已经见过弗里德曼博士26年了。因此,我没有尝试过很多其他事情,只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人。尽管有一段时间,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不得不离开他的诊所约六个月,而我去看一个进行认知行为疗法的人,因为我很好奇它是否会对患者产生巨大影响我的幸福,那时感觉很脆弱。我觉得这种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无用的。我感觉好像看到弗里德曼博士和我离开时想:“哦,好吧,他给我发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但我可能可以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在那儿,正在注意,所以当我开始陷入另一轮沮丧时,有人知道我,知道我正在经历的事情,也知道我过去经历的事情,谁会说:“我为此感到担心。而且,如果您要举报,那就是个问题。”非常稳定。并且它的一致性非常稳定。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和同一个人一起做的事实。他非常了解我。他知道关于我的某些事情,其他人真正都不知道。他和我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而且他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怀疑最终将需要退休或退出我们共同完成的工作。
他看到我经历了最严重的灾难,他经历了我找到丈夫,生孩子之前的那段时期,或者在我那时……我的生活比现在感到更加脆弱的时候。而且我不认为我能够与其他人建立这种关系。尽管我敢肯定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助我。但是考虑到我的波动-即使我感觉很好-我认为去那里真的很重要。我必须说,它通常也很有趣。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好吧,失去这种关系肯定会在时机成熟时蒙受巨大损失。
安德鲁·所罗门:
我希望他不会在我年老的父亲去世的同时退出。我希望这些事情不会同时发生。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当然。当然。关于数字心理健康治疗的想法怎么样?您对提供自我指导的抑郁症培训或其他类型的数字化治疗方法有很多想法吗?
安德鲁·所罗门:
我认为对于因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而无法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方法的人,数字治疗具有一定的潜力。我认为它的用处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我认为抑郁症的真正治愈是由于医学干预(无法通过数字方式进行的),药物或其他手段造成的。或者是建立任何人际关系的结果。
我的意思是,即使是我自己,而且我与周围的人之间都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我觉得Freedman博士帮助我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我认为,很多沮丧实际上是在数字环境中而不是在直接环境中频繁互动的结果。
您知道,有一项研究让我着迷,其中有一群非常年轻的孩子(他们来自非亚洲背景,我认为是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女人来用中文和他们交谈。每周一次与他们一起玩一个小时。她做了一年。然后另一组孩子也有一个女人,说了很多相同的话,但是她在屏幕上。和孩子们一样,孩子们也被屏幕迷住了,非常仔细地看着她,但是她是在屏幕上而不是亲眼看。到了年底,他们对孩子们进行了测试,亲自拜访的孩子们可以区分所有使用普通话所必需的音调。而且看屏幕的孩子无法识别任何会说普通话的音调。
我只是不认为数字化存在是可比的。我认为这很有用。我认为它可以作为补充。我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可用的方法会有所帮助,但是我认为您将不会拥有直接交互所具有的强大功能。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听起来您也感觉到,即使对于现有的数字媒体治疗,关系的某些组成部分对于他们获得的成功也至关重要。
安德鲁·所罗门:
我不想说这对他们取得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我想说这通常对人们寻求的成功有很大帮助。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很公平。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当您的孩子长大时,您如何发现与他们谈论心理健康(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总体上的心理健康)是否有帮助,甚至为他们准备了解如何与孩子保持联系提供了帮助自己健康吗?
安德鲁·所罗门:
这是微妙的平衡。我的孩子分别是12岁和10岁,我想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遭受任何形式的精神健康挑战,他们应该可以随时来找我并与我交谈。而且我对此很开放。他们知道我患有抑郁症。他们知道我服用抑郁症药物。我不时与他们讨论过。
我不想让他们沉迷于我的沮丧之中,以至于他们曾经感觉到我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个不稳定的人物,并可能突然消失。我认为孩子们往往会很快跳入这些挑战中任何一个的灾难性逻辑。
因此,当我与他们交谈时,我很开放,我说:“您知道,有一天您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如果您愿意,我希望您能来跟我讲话关于他们。我确实得到了医生和药物的帮助,而且我的状况还不错,依此类推。我试图以一种非常冷静,合理,不过度使用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德里克·赫尔(Derrick Hull):
完善。好吧,安德鲁,我感激不尽。坦白地说,无论是个人还是Talkspace团队中的其他人,都为这次面试做准备,并感谢您的宝贵时间和慷慨的精神,并与我们分享您的经验-与您交谈很高兴。
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最新的书是遥不可及:从变化的边缘进行报告,这是他的国际报道和可听见的原声的集合新的家庭价值观借助数十次亲密访谈,重新定义了成为当今美国理想家庭的含义。
安德鲁,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您,祝您好运。
哪个人因恐鸟症而闻名
安德鲁·所罗门:
非常荣幸。谢谢。